83 岁的徐小虎,可能是艺术史界唯一敢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
2020-02-29

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建立一部完整的“中国绘画真迹史”,和“没有大师的艺术史”。
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 83 岁,蓝袍银发,说话时的自称在“我”和“小虎”之间来回切换。这个艺术史学者在全球学界皆属于异类,只因她最爱做戳穿皇帝没穿衣服的小朋友,而“皇帝”往往是学界公认的研究方法,以及结论。
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呢?
作家阿城对此的评价是:“徐先生做一件事情,非常重要。虽然徐先生方法论的东西是比较早的发生,但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都还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是个新的方法,她确立了这个方法。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按照这个方法继续走。因此,我说徐先生是立代的。她是立了一代。之前的方法,我个人看来,显然没有徐先生的完备。”
虽然徐小虎的导师不喜欢她的方法,“立代”终究开始了。这本叫做《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的书同时带来争议和(相比之下少得多的)认可,并帮助她获得了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博士学位,得到了欧洲的亚洲艺术史权威 Roger Goepper 、荷兰伦勃朗研究所所长 Ernst van der Wetering 和伦敦大学研究员 Paul Taylor 等人的推荐。
陈丹青的评价是:“徐小虎针对古画真伪的个案进行研究,具体到某个疑点,这是极其枯燥漫长、虽然充满惊喜但很不讨好的工作,堪称‘兴奋完了就遭罪’,但是她坚持了五十年。”
坚持的代价当然很大。她大学就读于美国班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 Vermont),之后去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中国艺术史,师从方闻。在这里,她接受了作为艺术史学者最初的学术训练。但因和方闻意见不合,后被开除。
离开普林斯顿后,她来到了日本,待了 4 年。 1971 年,徐小虎回到美国,对旅美书画收藏家、鉴赏家、画家王季迁先生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采访; 1980 年,她来到台湾,一边研究台北故宫所藏的传统书画,一边在台湾大学任教。她开始形成自己鉴定中国绘画的方法。
自此,她的三段经验——普林斯顿所受的“结构分析法”的训练,日本形成的不重名而重美学的鉴赏态度以及对古画严谨的物理检查,从王季迁访谈中得知的经验心得——变成了一个综合的方法论,而这个方法论推导出一系列结论。比如,书法史上的名作《自叙帖》不是唐怀素的作品,而应该是明代人的书法;台北故宫存世的列入“元四家”之一吴镇名下 50 多幅作品中,只有三张半是吴镇的真迹,等等。
这就是《被遗忘的真迹》的由来。她的观点惊世骇俗:“艺术史的任务是厘清艺术品的时代关系,但我们今天的艺术史很多是为大师写传,我们可能弄错了自己的任务。艺术品它们不需要归在某个大师名下,我只把它们当作一个器物一个作品本身,研究它演变的历史,把它们的前后关系研究清楚。我觉得要找到真实,我要的是很正确地看那张画。”

徐树铮(1880—1925),来自:维基百科
这本书也让她觉得自己对父亲和祖父有了交代。她的祖父徐树铮是北洋军阀皖系将领,因 1919 年收复外蒙古而名声大振。父亲徐道邻是留学德国的法学家、民国宪法先驱,担任过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等职。母亲芭芭拉(中文名徐碧君)则是父亲留学时结识的德国人。
今年 10 月,徐小虎的中文新书《南画的形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得以出版。这本书对 1799 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绘画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从文人画在中国的发展和在日本的接受与转化,探讨日本南画的形成。
而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建立一部完整的“中国绘画真迹史”,和“没有大师的艺术史”。
以下是她的一些口述,我们归类呈现,可能和原话有些出入,特此告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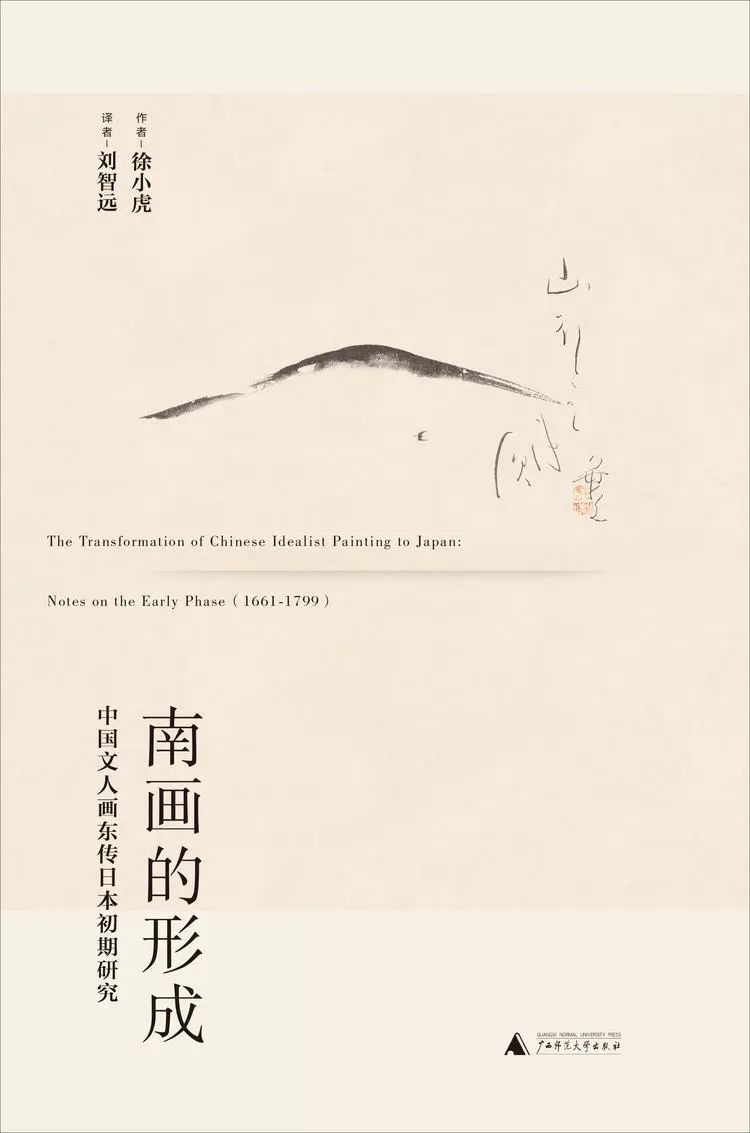
关于权威和真实
1、我小时候就认为大人很笨。因为他们说的话常常随从着一种不真实的价值观,好像你这个脚应该裹小一点、你考试考了 45 分,人家会怎么想啊?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呀?他们大人如果坚持这样子想又怎么了?这条命是我们的,我们必须自己去活它才对。
2、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日本人没有抄袭古人的习惯,也没有工匠远不如大师的观念。但是有时候对外,在国际舞台上,他们的艺术节,官方要做假的,表示日本的艺术是现代的。他们所谓的现代是西方样式的,这个想法太奇怪了。
3、传统鉴定法一直说皇帝穿着衣服。第一就提出那个款,错的就是款,画是真的。画是每一个人真的画出来的嘛,可是那个人是什么?那个款是假的,可是大家都以这个款来开始。这些所有的大人他们都是这么讲。
(所以)你要看看每一个时代有他不同的结构方法,比如鸡蛋跟那个玉米的关系就会画的不一样。鸡蛋特别大,玉米特别小,或者怎么样?它在二度空间里要表示出三度空间,还是要表示出二度空间?还是只是笔墨本身?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做法。
我就想用检查陶艺的态度(来检查画)。中国人他很会检查陶艺,他摸了就知道了。可是(对于画),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是看外面那个盒子上面说——苏东坡。那因此就是苏先生的大宝贝了。被骗了,一开始就被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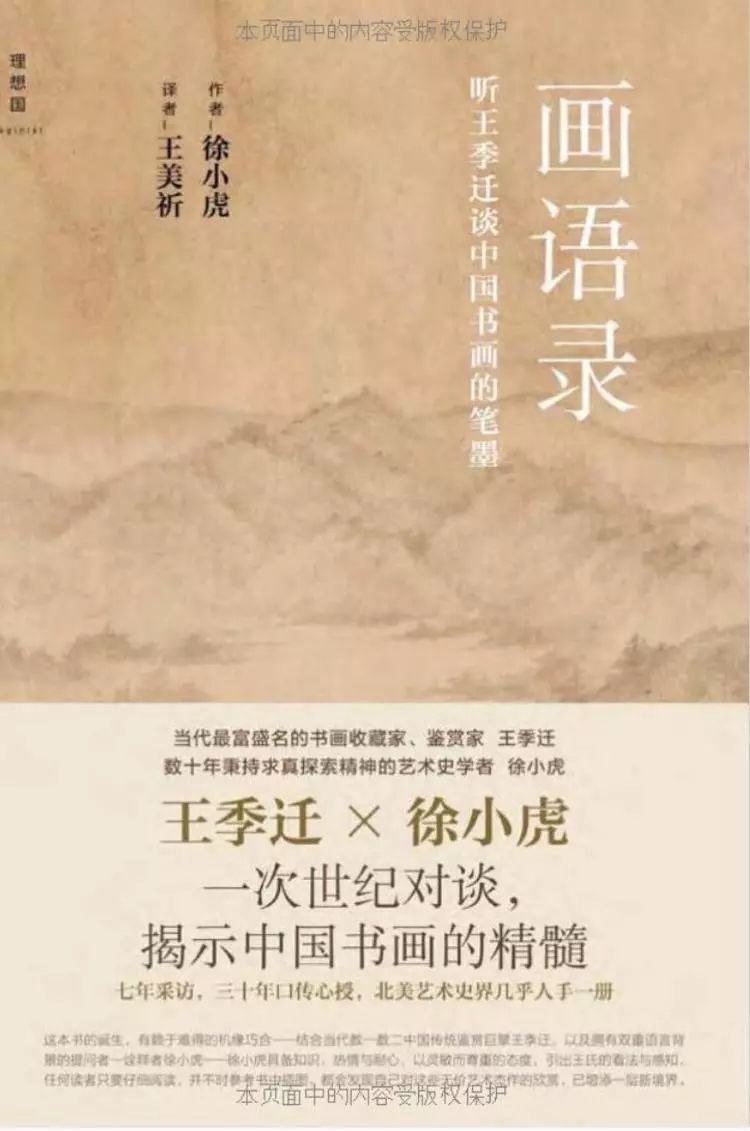
4、现在日本最有名的两个艺术家都不是艺术家。一个叫村上隆,另外一个叫草间弥生。他们两位赚的钱多得不得了。一个人(指草间弥生)就是自己的身体。每天早上就是有这种强迫性的神经运动,非做这些东西,每一点画下来都是活的。可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形而上的一种表达,她只是在画这个洞,就—像—我—在—吃—饭(声音拉长),我就吃给你看,这不是艺术。
另外一个人印出来的这些画,就像个窗帘。

草间弥生,来自:flickr
5、(如果年轻人要了解艺术史),第一,不要看书。看书是要看的,不要先看书。当考古学家也是,他们先看书再去挖,然后挖出来一个叉子,他们就说这是某某人的什么,这就太糟糕了。你要先看东西,先看了这个东西,仔细地去看,用你自己的心,自己的眼睛去看,会(萌生)很多问题。为什么是红的?是什么意思?来自哪里?等等。
经过自己跟艺术品彻彻底底的沟通之后,你再去看书。然后发现书里说的完全不一样。那这个书说的是老师说的,要不然就是古人说的,最要紧的是跟这个作品同时的人所说的。宋朝人形容文同,怎么形容?然后我到故宫去看,这个文同的竹子是这么死板,这么的机械性,这么的重复,这么的笨,这个笔是那么秀气,那就跟他们所说的完全不一样。那你就知道当时的人所看到的文同和现在在我面前的文同(不一样了)。这一张画,名字错了。
关于父亲和家庭
1、我小时候在重庆歌乐山,坐在小板凳上,听我奶奶讲《三国演义》,讲岳飞、《西游记》,她都会讲,和讲我爷爷一模一样的精彩,到蒙古去,等等。当然我觉得蛮惭愧的,因为他们都是这种传统学者,二十五史,唐诗,宋词,大概八岁之前都背下来了,到十三岁又温习了一遍,到二十几岁就一辈子不忘了。我是连看都没看,所以觉得很惭愧。
2、父亲的影响当然很厉害。我的一辈子,父亲离开家里,他为了国家,每一个都是蒋委员长这个,蒋委员长那个。因为他是蒋委员长的秘书,蒋委员长到哪他就到哪,(都)不在家。
3、(离开中国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的时候,初三。 1949 年 5 月 27 号。这是第二次我站在船头看着我爸爸在岸上,我又感觉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他了。第一次是南京大轰炸的时候,妈妈抱着我看着爸爸,一大群人站在那儿,我哭啊哭啊哭啊,觉得一辈子看不到他,一整年没看到他,对一个三岁小孩子来说是一辈子了。后来 15 岁离开的时候,又觉得那一辈子更长。(再后来)他来(美国)的时候,我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
4、(1949 年前后),我就问他,“你可以帮忙的,你为什么不帮忙?你有那么多政治经验。那人家刚刚从农村出来的,他们懂什么?”爸爸说,“就是为了这个,我没办法在那边工作。第一,他们三次叫我去参加共产党建国。可是我不能,因为我发誓了,我是国民党党员。我说,可是你这个蒋委员长不好啊。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孔子派不是孟子派。他就跟我解释孔子、孟子不一样。他说,孟子说,只要蒋委员长不好,他就不应该做。那孔子派是蒋委员长不好,我再谏说谏说。他要沉下去,我是跟他一起下去的,我是一直不会离开我的主,所以我就是忠于我的党。”

徐道邻(1906—1973) 那些我们不明觉厉的艺术见解,可能你会觉得有用
1. 关于唐五代、北宋、南宋、元、明、清这些朝代的绘画精神
简单来说呢,唐是一个大帝国的宇宙观。每张画,即使是坟墓里头的东西,就是死人躺在那,你还是会有远远的山,远远的日落或者日出。整个宇宙就是一直到边缘。它的看法不是这个床,床边的几朵花,它是一个大大的(宇宙)。
然后从五代、北宋,我们只有大概五张画。五代有一个,就是一个竹石。你从这个里头就会感觉到,透过画本身,整个宇宙的价值,宇宙里头的神气、神的存在比人大。他是透过绘画本身来表达,远超越人的大神存在,很棒的!不管他画的是竹子还是画的是山水,那个震撼是很厉害。
从那个时代一直到现代,直接下坡,越来越不是神,越来越是人。然后人还不够,还有人的家具,里头有什么东西?他的小玩意,他的互动,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有,就是小小的,像 gossip 、谣言那种样子,看他们在干嘛。
然后就到了 20 世纪,就是设计或者反讽。我们对这个的不满,那个的不满,很少很少是在歌颂宇宙的美,歌颂神的存在。我们的生命价值是多么的可爱,就是要喜爱这个生命,要多多地跟神联络。这个没有了,所以物质化到底了。

元,吴镇,《双桧图》
2. 关于《南画的形成》
当时是写给高居翰(James Cahill)和岛田修二郎老师们的,来补充一下高居翰给我们介绍的日本南华篇。南画是他介绍给美国的,他从前在日本不断地学中国艺术史,他在日本发现了就是有这种东西,觉得很好玩,就收集了南画,也就做了一个展介绍。然后我看他的解释,就好奇这些东西的来源。
那个时候,德川时代和清初,两个国家彼此没有交通来往,在官方,那么大的影响到底如何跑进去的呢?然后日本画家怎么画出来的和中国的南宗画一点都不一样?即使在外面很像,里头一点都没有同样的意思。因此这本书是关于一种价值观上的误解所形成出来的一种事实在视觉上的变化。
他们不但说他们画的是某种东西,而且要用某一种特殊的中国笔法,但在日本又没有笔法这一概念,更没有中国笔法的习惯。因此突然采取了中国二三手、已长达数百年的复古性的文人画传统……又不能和华人面谈讨论。
北宋士人画画说,我们画画不是画实物,是画那个东西的精神,把山水的精神带出来了。可是那个元朝人就误解了,他们误解了士大夫的精髓,说我们画画是把我的精神带出来了。他们的宇宙缩小了,整个用笔就不一样了。之后,明朝人说我们画画是画元朝人的笔意,又根本地完全误解了,就开始抄袭,在功二手艺术,整个艺术就被裹脚裹脑裹心了。于是创造就没有了。

徐小虎,来自:个人官网
文人画运动根本就是个很不健康的概念及行为,没有任何政府要求你做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好,他们自己说好,然后就跳到这个陷阱里头去了。就是不知不觉人会离开真实,离开真理,就是为了要,不是好奇,怎么说?他们不是用自己的心跑出去探讨一个事情到底如何?他们是穿别人说过的衣服,说别人说过的话,说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二手第三手这种又听错了,那个传言就越来越假,越来越不真。
可是越来越热闹,几千几万个人都说:啊,我们崇拜的是某某某的笔意。搞到这个样子,就是完全误解真实,随从这一个无聊的价值观。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误解的传播和影响。
可是在艺术上,他们在没有经过元四大家之偶像化过程的日本,根本不可能真的关心。你画了个有点披麻皴的山水,名字错了,叫它黄子久笔意,倪云林笔意,甚至于董源或李成笔意, 有名字的全新作品,在笔墨上与中国古画无关。

池大雅的作品,来自:维基百科
3. 关于日本人和中国传统
关于南画,这些来自中国的大和尚很伟大。当时日本人在政府的指示之下得学习汉文化,采纳“忠”的观念。要用忠这个字,要日本人像中国人般很爱他们的国家,特别忠于他们的将军 Shogun ,所以将军当时就到处设汉学府 。
当时很多艺术家就跑到宇治(Uji)那里新设中国大庙。黄檗宗万福寺(Manpukuji)是福州檗宗万福寺的一个分寺。那边的和尚就是晚明的人嘛,万历年代那种。那时候那些书法画竹子的时候用笔的结果又厚又重又笨又多又挤。
日本艺术家也就乖乖去抄,又重又厚又挤。这个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的不舒服,他们抄华人的样本的时候,画的很像,可是他们画自己的东西时就不一样了。日本用笔比较轻松的,比如池大雅(Taiga no ike)发明的那个半蘸墨(katabokashi)——笔就是一半墨一半水,很清晰。他不喜欢重叠,不喜欢杂味儿,日本审美观喜欢纯的,所以他们受中国的影响其实极少。

五代,徐熙,《雪竹图》
因为他们没有相信必须画出黄子久的笔意才能变成一个高尚的画家。这是中国人的想法。他们觉得要画黄子久的笔意,那我们试试看,稍微两三笔,就把它简化了,忽然又变成轻松好看了。可是他们乱说嘛,他们就说我是学倪云林、学李成。他根本没看过原作,就是好玩嘛,是一个新的,外来的稀奇的新经验罢了。没有原来的社会价值。 但在大雅的手里却发出了一朵新鲜活耀的大花。
他们会抄,可是把那个抄下来的东西,他们会把它完全变成自己的生活,不放弃他们内在的生活。我们可以看现在日本,美国有什么,他们就有什么。穿衣服都是叫穿西装,办公朝九晚五。这个就是他们给外面世界做的事情——西方行为。

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 艺术是要跟神性相连
艺术的目的是来做一种神的沟通。我们自己的灵魂里头所能表达的最高神的存在就会从艺术里出来。即使我死了三百年、五百年,你看到了就感觉到了。你看我们范宽《溪山行旅图》,看了就会感动不得了,好像看到佛、看到神。其实它是一座山。为什么看到了感觉它是神?就是他画出来那个神的感觉,透过山本身(表现)。所以当时形而上的这个神的传达,就透过时空会到我们。现代人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艺术。我不认为它是艺术。它是商业吧。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支持公益传播,所转内容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告知,我们会立即处理。